366小说>被公用的白月光 > 第41章 第 41 章 致死量的修罗场(第4页)
第41章 第 41 章 致死量的修罗场(第4页)
出了房间,程其庸询问保姆什麽时候离开的。
保姆回答:“天亮没多久就出去了,喊他也不回应,不知道去哪了。”
程其庸哦了一声,这事便没有下文。
等到程以镣起床的时间,他冲出来,指着程其庸拍桌子大吵。
“你醒这麽早,为什麽不去把他找回来?那你醒了干嘛的?你就让他走?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你只是享受跟我抢东西的感觉!你太恶心了,程其庸你就是最自私丶最坏的那个。”
程其庸擡眸扫了一眼急得原地打转的程以镣,平静且傲慢地表示:“我去把他找回来?我不用哄他,我只要收紧他脖子上的链子,他就会自己来找我。”
没有任何征兆,程以镣的拳头直挺挺地打在程其庸的脸上。
程以镣指着他,破口大骂:
“你是最自私丶最坏的那个!”
这一拳打得程其庸眼睛瞪圆了,保持到现在的得体就像炸开的冰层,轰得一下——
程其庸揪起程以镣的衣领,把他撞在墙上,同时一拳重重地回击在人类脆弱的腹部,把人打得眼珠子都要突出来。
程以镣捂着肚子,眼睛涨得血红,血丝如蛛网盘踞。
程其庸冷哼,“程以镣,你什麽身份,他什麽身份?”
程以镣指着自己,声音干脆利落的从喉咙里冲出来,大大方方地咆哮:
“我什麽身份?我他妈就是贺松风的一条狗!”
他的手指又一转方向,点在程其庸的身上,尖锐地指下去:
“不如想想你是什麽身份吧!”
说完,程以镣冲玄关,扫走车钥匙匆匆赶出门。
“你不找,我去找。”
贺松风没有程以镣想象力好找,他忽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不在图书馆,不在寝室,哪里都找不到他。
程以镣找了他好久。
跟无头苍蝇一样,家也不回,整天泡在学校里寻找贺松风的蛛丝马迹。
时间推到临近小年前夕。
嘉林市是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多的地方,所以一到传统节日,这座城市就变成空城。
路上空空荡荡,谁来过,谁走过,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程以镣终于捕捉到贺松风的影子。
细瘦的手臂在胸前环抱一沓资料纸,他只穿了一件米色羊绒衫,宽松得似乎不是他的款式,好几次领口都被恶劣的北风刮下来,露出一侧又圆又白,像藕节似的肩头。
被北风以下流的姿态摸过肩头,他不慌不忙,等到北风摸够了,再不紧不慢地撩回来。
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撩人不自知的淡漠。
贺松风的头发又长了,披肩的长发被他用浅咖色的发夹收起箍在发顶,露出一节雪白光洁的颈子。
贺松风美得雌雄莫辨,就是这样的美,才能惊艳到程以镣一眼认出来。
程以镣赶紧追上去,就在马上要撞上的瞬间,他又好奇贺松风这段时间到底躲在哪里,于是卡着一个距离,跟随在贺松风身後。
贺松风在学校外的水果店里买了一些水果,看分量是2-3人份的。
在等店员切水果装盒的时候,贺松风把发顶的发夹摘下来,轻轻摆头理了理头发後,又把头发绕着手掌捏成一捆,随手夹回原位。
但依旧散了几缕不听话的头发在後颈,惹得贺松风蹙了眉头,净白的手指轻轻扫过後颈,轻柔地撩起并往後脑的头发里搭。
温柔的氛围将贺松风身边包围出一阵熏香,不再是廉价的肥皂水,而是麝香丶龙涎香于羊绒木的交织,又混着丝丝缕缕的皂角味,是独属于贺松风的慵懒宁静。
冬日都为他变得柔软。
不知道店员和贺松风说了什麽,贺松风接过包装袋的时候,脸上露出轻盈盈的笑,笑得那店员拿刀的手都抖了,脸蛋红红。
程以镣也看得嘴角忍不住的往上翘。
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贺松风提着双人份果切,直直地走进学校旁的星级酒店里。
更坏是,酒店经理和贺松风关系似乎很熟。
酒店经理帮贺松风接下资料纸和果切袋,走在前方哈着腰尽量让自己的气势不高过贺松风,领他进入酒店深处,帮他按下电梯按钮。
经理和贺松风有说有笑。经理说,贺松风笑。
贺松风看上去就是个被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他可以坦然平静的接受旁人的伺候与讨好,像习惯了似的。
等待电梯的时候,贺松风忽然擡手示意经理安静。
他扭头,缓缓盯着来时路,一条长长的走廊,光线炫目的从头顶投射,照得所有阴影无所遁形。
“怎麽了?”
“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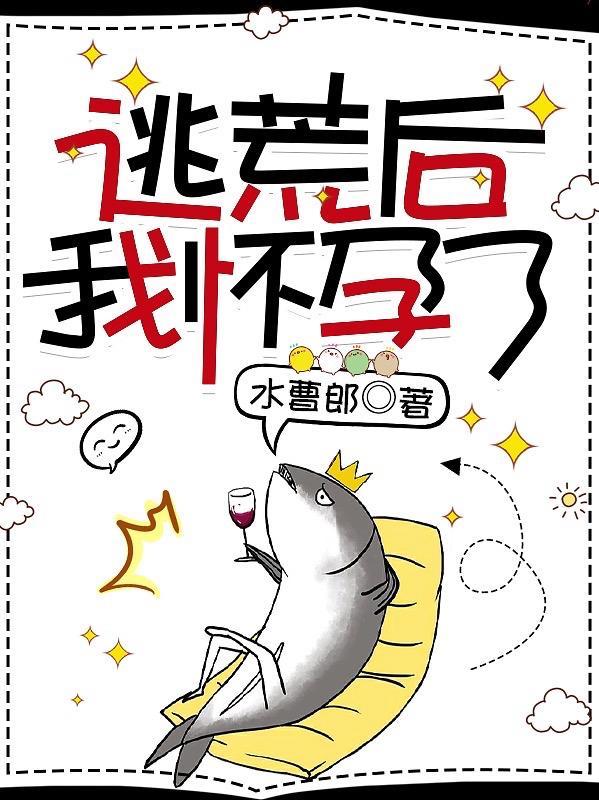
![漂亮反派拿了万人迷剧本[快穿]+番外](/img/5436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