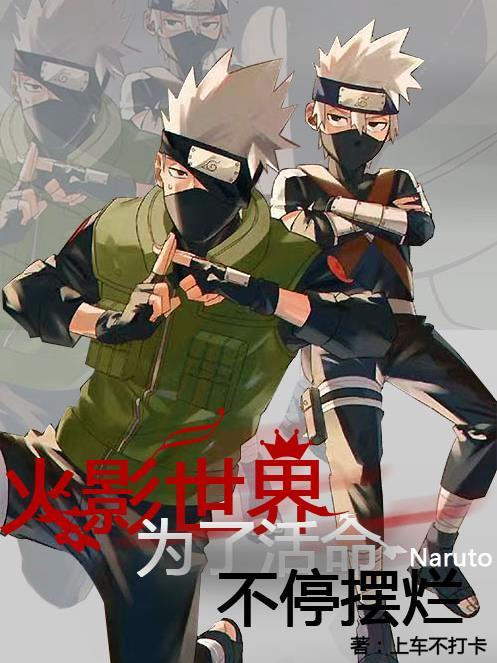366小说>愿为她裙下之臣【快穿】 > 阴郁病娇少年20(第1页)
阴郁病娇少年20(第1页)
沈蔚坐上回家的出租车的时候,宋循还一直在车后面盯着,一直看着车子远去,没入地平线之后再也看不见。
耳畔还回着她的声音:“就这样?”
“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都给你。”
少年的誓言轻轻浅浅,是风中极易飘散的烟,也是更古不变的日月,此时真心必是忠贞,爱意发自肺腑,直达灵魂。至于日后如何,端看时光如何雕琢。
不管如何,反正在当下,沈蔚是满意了。她看到了真心。有了这层关系在,她在挽回宋循的人生轨迹的时候也更有底气了。
刚才的各种不愉快一下子烟消云散,她笑眯眯地凑过去,揽着比她高一个头的男孩的脖子,在他侧颈上轻轻啄了一口。
“啵”,小小的一声。
“给你的奖励,刚刚说的话很好听。我喜欢。”说完这句话,沈蔚松开他,看着呆楞住的少年,莞尔一笑。
“明天见!”
留下最后一句话之后,沈蔚迅速向身后跑去,司机师傅已经等候多时了,不好再让人家等。
她的长发因为风飘起,松松地把发丝送到爱人的手掌心。
宋循感受着手心麻麻痒痒的感受,看她远去的倩影,心里像是被人挖去了一大块一样,感觉自己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了,一心只想要随着拿走他的心的那个“偷心人”去。
但是这是不现实的。
恍惚了片刻之后,宋循终于理智回归。
沈蔚才刚刚十八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就算他搬到她身边去,也没有办法和她住在一起。而且他混不吝惯了,但是怎么也要为她想想。
她是人见人爱的优等生,但是他却臭名昭彰。
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别人的看法的宋循,也会为了喜欢的女孩子开始考虑人情世故,在乎世俗的评价;从来都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宋循,也会有朝一日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情愿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去取悦她。
怀着高兴又带着点隐秘忧虑的心情,宋循转身回去。到了大厅,他就直接从兜里把耳机拿出来带着,连屈尊降贵看徐美玲的意思都没有,摆明了非暴力不合作。
他这副桀骜的样子,差点又把徐美玲给气死。
虽然宋循很早就好像陷入了叛逆期一样,跟她说话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夹枪带棒的,现在长大了,不说难听话了,但是学会冷暴力了,只要徐美玲不强制让他说话,他能整整两个月都不跟她说一句话。
想到这里徐美玲心里就是一阵酸楚,她十月怀胎把这个唯一的儿子生下来,期间吃了多少苦头,挨了别人多少白眼。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她成了名正言顺的宋夫人。之前那个女人留下来的小孽种也被赶到英国去了,家里的产业以后就全是自己的儿子的。
明明好不容易他们母子俩才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荣华富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儿子却变了,他以前是
个多可爱的孩子啊,知道她辛苦,看到她一个人偷偷地哭的时候,还会抱上来,用他那双嫩呼呼的小手给她擦眼泪,跟她说“妈妈不要哭,我会赶快长大,保护你不被别人欺负。”
那个时候她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是生对了,他不仅仅是她用来谋求幸福的工具,是她一步登天的凌云梯,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和她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是和她血脉相连的人,是她生命的延续。他就像小太阳,在寒冷刺骨的的严冬,给予她温暖,让她不至于冻死。
那个时候她们多好啊,可是现在呢。。。
不自觉的,徐美玲想痴了,陷入在回忆中无法自拔。可是醒来的时候却还是只能面对宋循的冷脸,这样巨大的反差让徐美玲整个人都不好了,她受不了!
她直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蹬蹬蹬”地快步上前,想要拦住宋循。她个头不高,即使是这样,站在宋循面前也不过堪堪到下颌处。她伸着手拦他。
宋循漠然地看着她,注意到她踩着高跟鞋的步伐有些踉跄,看样子竟是不是很熟悉的样子。他经不住冷笑,小的时候,在徐美玲还有工作的时候,她也是经常穿着高跟鞋,即使那个时候她穿不起多么昂贵的鞋子,要把钱省下来给小宋循当学费。
那个时候,不去上学的日子,宋循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徐美玲怕他被人贩子拐走
,要么是把他关在家里,要么就是托付给邻居奶奶帮忙照看着。
宋循每天看到的,就是她踩着高跟鞋也一样走得摇曳生姿,神气十足的背影。每次在家里听到高跟鞋的声音,他都会特别高兴,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
徐美玲还煞有其事地跟小时候嫌声音吵闹的他说过:“高跟鞋是女孩子展现自己美丽的工具,是女人的战靴。只要有了她,妈妈就知道要挺直腰杆,她是妈妈最忠诚的伙伴。”
这句话,宋循一直记到现在,还有当时她说话的神态、语气。所以他现在才会觉得特别可笑,觉得嘲讽意味直接拉满。
现在的她,恐怕早就忘了她当初说过什么样的话了。她被男人养在家里,金丝雀一样,早就没有了自己的坚持和尊严。就连她当时口口声声说的,“高跟鞋是她的战靴”的话,估计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这副连走路都不太习惯的样子,好像脚上的鞋子不是她行走的工具,而是深重的枷锁一样。
现在的她,真的就只剩下被男人关在床上的价值了。
宋循想到这里的时候,也不禁讶异于自己的恶毒,他用这样的词汇,这样的句子去形容生养他的母亲,实在大逆不道。传出去,真的要被人唾在脸上的。
可是,
宋循看着徐美玲拦住他,涂着大红色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那个贱蹄子走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的唇纹一向很深,此时就算是被昂贵的唇彩点缀着,也看得很明显。那一条一条的纹路,像是蛇一样,不断喷射出毒汁,将他捆绑、缠绕,让他堕入深渊,喘不过气来。
他麻木地想:早在十二年前,他们这对母子,就该一起下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