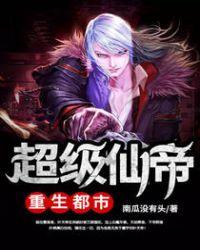366小说>军阀崛起:八美同堂定民国 > 第2章 乡韵凝芳苏玉婷的乡绅家与守土心(第1页)
第2章 乡韵凝芳苏玉婷的乡绅家与守土心(第1页)
(一)苏家大宅:临郊望族,耕读传家
光绪二十七年,秋。
临城县西南三十里处,有个名叫“苏家堡”的村落。村子三面环山,一面傍水,村口矗立着两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下是青石板铺就的晒谷场,也是村民们议事聚会的地方。村子中央,坐落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宅院,青砖黛瓦,高墙深院,门楣上悬挂着一块黑漆鎏金的“苏氏宗祠”匾额,两侧则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这便是苏家的祖宅,也是苏家堡乃至周边十里八乡最具威望的府邸。
苏家并非临城土着,祖上是明末清初从山西迁徙而来的商户。起初,苏家只是在村里开了家小杂货铺,凭借着诚信经营和精明头脑,渐渐积累了第一桶金。到了乾隆年间,苏家先祖见种地是长久之计,便大量购置田产,做起了地主。历经两百余年繁衍,苏家已成为临城周边数一数二的望族,田产遍布苏堡村及周边五个村落,共计三千余亩,家中雇佣的长工、佃户过两百户,还有两座小型油坊和一座粮铺,家底殷实,却从不张扬。
与其他地主不同,苏家历代坚守“耕读传家”的家训,既重农耕实业,也重诗书教化。苏家大宅不仅有存放粮食的仓库、饲养牲畜的棚院、处理农事的账房,还有专门的书房和私塾,族中子弟无论男女,都要读书识字,明事理、辨是非。苏家人丁兴旺,却始终和睦相处,对待佃户和长工也格外宽厚,逢年过节会送米送面,遇到灾年便减免租税,因此在地方上口碑极好,苏老爷苏振邦更是被乡亲们尊称为“苏大善人”。
苏振邦是苏家第十八代传人,生于同治十年,年轻时曾考取过秀才,后因父亲病逝,便放弃功名,回家主持家事。他身材魁梧,面容黝黑,常年穿着一身粗布短褂,脚踩布鞋,看起来更像个庄稼汉,而非坐拥千亩田产的乡绅。但他眼神锐利,心思缜密,做事雷厉风行,又不失宽厚仁慈。在他的打理下,苏家的田产不断扩大,生意也蒸蒸日上,同时还牵头修建了村里的学堂、祠堂和石桥,深受乡亲们的爱戴。
苏振邦的妻子赵氏,是邻村赵家的女儿。赵家也是耕读世家,赵氏自幼温柔贤淑,勤俭持家,与苏振邦成婚三十余年,夫妻恩爱,共育有两子一女。长子苏玉成,性格沉稳,跟着父亲打理田产和生意;次子苏玉安,聪慧灵动,被送进临城学堂读书,希望能考取功名;小女儿便是苏玉婷,生于光绪二十七年,是苏振邦最小的孩子,也是他最疼爱的掌上明珠。
苏玉婷的出生,给苏家带来了无尽的欢喜。苏振邦中年得女,对她宠爱有加,却从不娇惯。他常说:“女儿家不必拘泥于闺阁,多学些本事,方能立足于世。”因此,苏玉婷从小便跟着父亲和兄长们一起,出入田埂地头、账房商铺,接触农事、商事和村务,并未像其他大家闺秀那样,被束缚在针线女红之中。
苏家大宅的布局,处处透着“务实”二字。前院是处理公务的地方,设有账房、会客室和私塾;中院是内眷居住的厢房,苏玉婷的闺房在中院东侧,取名“勤耕斋”,与其他小姐的“绣楼”截然不同——房间里没有精致的梳妆台和华丽的摆设,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宽大的木桌,上面摆满了账本、算盘、农具模型和几本农书、商经;墙上挂着一幅《苏堡村田产分布图》,是苏振邦亲手绘制的;窗边摆放着两盆仙人掌,耐旱好养,透着几分坚韧。
苏玉婷的童年,几乎是在田埂上和账房里度过的。春天,她跟着父亲去地里查看麦苗长势,学习辨认庄稼的好坏,听父亲讲解灌溉、施肥的技巧;夏天,她在麦场上帮着收麦、扬场,跟着账房先生学习记账、算账;秋天,她跟着兄长去粮仓查验粮食,学习分辨粮食的干湿、纯度;冬天,她在账房里整理一年的账目,跟着父亲处理佃户的租税纠纷,听他讲解如何安抚乡邻、化解矛盾。
赵氏虽然希望女儿能多学些女红,但见丈夫和女儿乐在其中,也便不再强求,只是偶尔教她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其余时间都任由她跟着父亲“抛头露面”。苏玉婷也争气,不仅学得快,而且悟性高,十岁便能独立记账,十二岁便能分辨出不同土地的肥力和适宜种植的庄稼,十四岁时,已经能帮着父亲处理一些简单的佃户纠纷,说话做事有理有据,连村里的老人们都称赞她“有苏老爷的风范”。
(二)乡野成长:习得务实,心怀乡邻
光绪三十三年,春。
六岁的苏玉婷穿着一身粗布小褂,扎着两个羊角辫,跟在父亲苏振邦身后,踩着湿漉漉的田埂,查看刚种下的稻苗。春雨刚过,田地里满是泥泞,苏玉婷的小布鞋上沾满了泥巴,裤腿也被溅湿了,但她毫不在意,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问:“爹,为什么有的稻苗长得高,有的长得矮呀?”
苏振邦蹲下身子,指着田里的稻苗,耐心解释:“这就像人一样,有的身子骨壮,有的身子骨弱。长得矮的,要么是种子不好,要么是根没扎稳,要么是地里的养分不够。我们做庄稼人,就得细心,把这些不好的苗拔掉,给剩下的苗多施肥、多浇水,它们才能长得壮,秋天才能多收粮食。”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苏玉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拔掉了几棵瘦弱的稻苗。阳光洒在她黝黑的小脸上,汗珠顺着脸颊滑落,她却笑得格外灿烂。从那天起,她便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踏实感。
随着年龄增长,苏玉婷跟着父亲接触的事务越来越多,也渐渐明白了“责任”二字的含义。苏家坐拥千亩田产,看似风光,实则肩负着两百多户佃户和长工的生计。每年开春,苏振邦都会提前准备好种子、农具,分给佃户;遇到旱灾、涝灾,他会亲自带着乡亲们兴修水利、抗旱排涝;年底收租时,他从不强逼佃户交租,遇到家境困难的,便允许他们缓交或减免。
苏玉婷记得,她十岁那年,临城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许多佃户家断了粮,纷纷来到苏家大宅求助。苏振邦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开仓放粮,给每户佃户放三个月的口粮,同时减免当年所有租税。
那天,苏家的粮仓前排起了长队,乡亲们拿着布袋、竹筐,脸上满是感激。苏玉婷跟着父亲和兄长们一起,给乡亲们分粮。她看到一个白苍苍的老奶奶,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颤巍巍地走来,小男孩饿得直哭,老奶奶一边抹眼泪,一边不停地给苏振邦作揖:“苏老爷,您真是活菩萨啊,救了我们祖孙俩的命!”
苏玉婷看着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心里五味杂陈。她拉着父亲的衣角,小声问:“爹,我们把粮食都分给乡亲们,我们自己怎么办呀?”
苏振邦摸了摸她的头,语气坚定地说:“玉婷,我们苏家能有今天的家业,全靠乡亲们的辛勤劳作。乡亲们有难,我们不能不管。只要人在,田地在,明年好好耕种,粮食还会有的。可要是人没了,再多的粮食也没用。”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了苏玉婷的心里。她明白了,苏家的财富,不仅仅是田产和粮食,更是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作为苏家的女儿,她有责任和义务,守护好这份信任,帮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从那以后,苏玉婷更加用心地跟着父亲学习处理村务。她跟着账房先生学习如何合理分配粮食、计算租税,确保公平公正;跟着村里的老把式学习如何识别天气、应对自然灾害;跟着父亲学习如何调解纠纷、安抚人心。她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总能现别人忽略的问题。
有一次,村里的两个佃户因为一块田的地界问题吵了起来,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动了手。苏振邦当时正在临城办事,苏玉婷得知后,主动跑去调解。她没有像大人那样呵斥双方,而是先让他们各自冷静下来,然后拿出苏家的田产账本,对照着图纸,一点点核对地界,又找来村里的老长辈作证,最终查明是其中一个佃户不小心越界耕种了半分地。
苏玉婷当着众人的面,清晰地说明了情况,然后提议:“李大叔,张大叔,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为了半分地伤了和气。不如这样,张大叔今年种了李大叔的半分地,秋收后把这半分地的粮食分一半给李大叔,明年再把地界重新划清楚,大家看怎么样?”
她的提议公平合理,双方都没有异议,一场纠纷就这样化解了。乡亲们都称赞她:“玉婷小姐年纪不大,办事却这么公道,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除了处理村务,苏玉婷还跟着兄长学习经营苏家的油坊和粮铺。她学会了如何挑选油料、控制火候,如何分辨粮食的品质、制定合理的价格。她现,油坊的工人在榨油时,浪费现象严重,便提议改进榨油工具,同时制定奖惩制度,鼓励工人节约油料;粮铺的粮食储存方式不合理,容易受潮霉,她便跟着父亲一起,研究出了通风、干燥的储存方法,减少了粮食的损耗。
在苏振邦的言传身教和乡野生活的磨砺下,苏玉婷渐渐长成了一个务实、聪慧、有责任心、心怀乡邻的少女。她没有大家闺秀的娇弱与矫情,多了几分庄稼人的坚韧与豪爽;她不擅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却精通农事、商事、村务,懂得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解决问题;她外表看似泼辣干练,内心却温柔善良,始终把乡亲们的疾苦放在心上。
(三)家世渊源:两百载基业,守土安邦
苏家的家世,远比表面看起来的“地主乡绅”更为深厚。苏家先祖迁徙至临城后,不仅积累了财富,更在乱世中坚守着“守土安邦”的信念。明末清初,战乱频繁,盗匪横行,苏家先祖曾组织乡勇,保卫村落,抵御盗匪和散兵的骚扰;乾隆年间,临城遭遇洪水,苏家先祖牵头募捐,组织乡亲们修建堤坝,拯救了下游十几个村落;道光年间,捻军过境,苏家先祖打开粮仓,接济逃难的百姓,同时组织乡勇配合官府,保卫县城。
两百多年来,苏家始终坚守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在乱世中守护着一方水土和百姓。这种“守土安邦”的基因,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融入了苏家人的血液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苏振邦的祖父,便是一位传奇人物。咸丰年间,捻军攻破临城,四处劫掠,苏振邦的祖父苏明远,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却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由苏家佃户、长工组成的乡勇队,凭借着熟悉地形的优势,在苏堡村周边的山林中伏击捻军,多次击退小股捻军的进攻,保护了苏堡村及周边村落的百姓。
后来,捻军主力来袭,苏明远知道仅凭乡勇队无法抵挡,便带着乡亲们退守山中,同时派人向官府求援。官府援军赶到后,苏明远又带着乡勇队配合官军,夹击捻军,最终将捻军赶出了临城境内。战后,官府为了表彰苏明远的功绩,授予他“武德骑尉”的荣誉官衔,并赏赐了匾额和银两。苏明远却婉拒了官衔和银两,只接受了匾额,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只是为了保护乡亲们的性命和家园。”
这块“护境安民”的匾额,至今仍悬挂在苏家宗祠的正堂,成为苏家世代相传的荣耀,也时刻提醒着苏家人,肩负着“守土安邦”的责任。
苏振邦从小便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深受其影响。他常对子女们说:“我们苏家能在临城立足两百多年,不是因为有钱有势,而是因为我们始终记得,要保护乡亲们,守护这片土地。在乱世中,只有大家团结一心,才能活下去。”
在这种家世渊源的熏陶下,苏玉婷从小就对“守土安邦”有了深刻的理解。她知道,苏家的财富和地位,是建立在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之上的,一旦遇到战乱和灾难,只有保护好乡亲们,才能保护好苏家的家业。因此,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兄长们一起,学习如何组织乡勇、如何应对危机。
苏堡村的村外围,有一道两米多高的土围墙,是苏家先祖组织乡亲们修建的,用于抵御盗匪和散兵。围墙外挖有壕沟,平时干涸,雨季则蓄满雨水,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村里还设有了望塔,每天都有村民轮流值守,一旦现异常,便敲响村头的大钟,召集乡勇集合。
苏玉婷十五岁那年,跟着父亲和兄长们一起,参加了村里的乡勇训练。她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躲在家里,而是穿上粗布军装,拿起长枪,跟着男人们一起练习射击、刺杀和队列。起初,村里的一些老人们有意见,说:“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子?”
苏振邦却力排众议:“乱世之中,不分男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玉婷是苏家的女儿,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保护乡亲。”
苏玉婷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训练时格外刻苦。她虽然身材纤细,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射击、刺杀的技巧进步很快,甚至过了一些男乡勇。她还利用自己的细心,现了训练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乡勇们的武器维护不当、战术配合不默契,便向父亲提出改进建议,得到了父亲的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