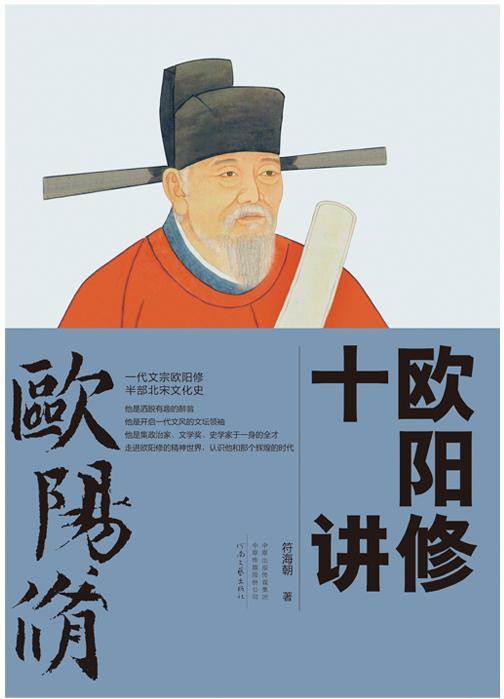366小说>贴身宠婢 > 平行番外二总裁x秘书5 表明心迹(第2页)
平行番外二总裁x秘书5 表明心迹(第2页)
对面的人也沉默地看着她,南枝却再也挨忍不住,擡手,捂住满是泪痕的脸,狼狈地呜咽出了声。
齐敬堂终究还是伸臂将她拢进怀里,抚抚她被细汗打湿的发,却并没有多说什麽,只任由她靠在自己怀里,为另一个男人流着眼泪,那时他才知道,原来沈知章在她心中那样重要,她会为他哭得那般伤心。
没有想象之中胜利的快感和欣慰,而是一种闷堵的压抑感,灯光下,齐敬堂垂下幽暗的眸,拿手指轻碰着她发烫的脸颊,他想,若有朝一日,她也会为自己哭得这般伤心,也不枉来这世上一遭。
可他不会让她哭,他不是沈知章,他有能力护好她。
齐敬堂一路将人扶进酒店里,她醉得很沉,整个人靠在他身上,像是种缠绵的依赖,发丝蹭在人脖颈上,痒痒的,还有淡淡的馨香,像是有只纤纤的手在人心口处挠啊挠。
齐敬堂将人放在床上,手抚上她绯红发烫的脸颊,她的呼吸沉而平稳,带着浓郁的酒气,齐敬堂也俯下身,停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他第一次这般近地看她的眉眼,无一处不喜欢,他也不知道是从什麽时候起,便被这个坚韧的女孩所吸引,她像株兰草,悠悠的,安静不吵闹,却就这样让人渐渐地离不开了眼。
手渐渐往下,指尖碰在她细白的颈,他轻轻摩挲,有些流连。
只要他静静勾开她的衣扣,便能解了他的魂牵梦绕丶辗转反侧。
他想拥有她,却不仅仅是她柔软的身体。
齐敬堂最终还是起了身,将被子盖在她身上,离开了。
南枝第二日醒来时头炸裂般疼,待瞧清了这屋里陌生简约的布置,慌张地起了身,见衣物都贴合地穿在自己身上才松了口气。
昨夜她早已喝断了片儿,想了半晌也想不出头绪来,恰此时门铃被按响,南枝穿着拖鞋去开了门,是位送早餐的服务生。
“薛小姐,有位先生替您订了早餐。”
南枝问他:“是哪位先生?”
服务生想了想,往单子上看了眼,答道:“齐先生。”
南枝微怔,然而关于昨夜,连一丝片段都捕捉不到,像是扔进海里的石,再也寻不见影,她坐回床上,打通了齐敬堂的电话:“齐总。”然而却一时不知该怎样开口。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薛秘书,给你放几日的假,好好休息。”
南枝却不知怎得,握着电话,泪又涌出来,带着哭腔“嗯”了一声,而後哽咽道:“谢谢您,齐总。”
待挂断了电话,南枝坐在床上,一时还有些空洞的茫然,突然从那种紧压的忙碌中抽脱出来,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空落,她草草将自己收拾了一番,走出酒店,却不知道要去哪。
她在街头随意走着,偶尔被身後的鸣笛声惊醒,往边上躲一躲。
如此不知走了多久,她觉得自己像这街上的游魂,每一脚都踩不到实处。
恰眼前恰是家便利店,南枝停下脚步,往透明玻璃里望,见一对情侣正亲昵地分食着一串鱼饼。南枝一时有些恍惚,仿佛瞧见坐在那儿的是自己与沈知章,他知道自己爱吃年糕福袋,每次点关东煮,总要要一串,最後吹一吹,喂进她的嘴里。
忽而那情景幻灭,那坐着的仍是一对陌生的情侣,南枝眼前模糊一片,再也不敢多待,几乎是落荒而逃,从街道上离开。
回到家里,仍旧随处都是另一个人的痕迹。她什麽都不想做,把自己蒙进被子里大哭了一回,後来不知什麽时候渐渐睡去,再醒来时,眼睛干干涩涩的痛。
南枝知道不能再这样窒息下去,将屋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把属于沈知章的东西都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一部分已失去意义的的扔掉,另一部分邮寄给了沈知章。
夜晚一夜无眠,她觉得屋里压抑得很。第二日仍旧上街上游荡,到了晚上,她终于明白再这样会将自己彻底消耗掉。
第三日,她强打精神,将自己拾掇好,回到了公司,企图以忙碌的工作将悲意与痛苦驱逐。
恰逢公司上手新项目,南枝一回来,便一连忙碌一整周。
只是她每每不在状态,不过强撑着,因此工作上每每出错,或是通知错了时间,或是漏发了文件,南枝不知自己什麽时候才能走出这样的状态,她仍旧用繁忙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使大脑不停地运转着。
这日下午,工位上的电话响起,是齐敬堂打来的。
“薛秘书,你过来一趟。”那声音带着些沉肃,南枝本能觉得不好,提起心神,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她进来时,齐敬堂正在电脑前浏览着计划书,闻听响动,眼从镜片後擡起来看向南枝。
南枝觉得今日的他比以往更要严肃些,周遭的气息也带着几分冷。
她一时屏息凝神,小心翼翼地擡眼看他,齐敬堂停了手中动作,身子微微往後靠了靠,擡目注视着她,沉默看了她半晌,直看得南枝头慢慢压下去,他才开了口:“薛秘书,还没有调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