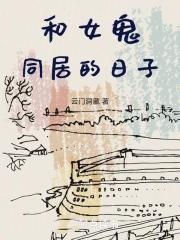366小说>满级外神回家,全身都是漏洞 > 番外8 极限拉扯(第1页)
番外8 极限拉扯(第1页)
宴追躲在水塘里,憋着气,嘴里含着一根芦苇换气。岸上,疤脸男人在吼叫:
“玛娜!你个废物!下去找!”
“扑通”一声,玛娜被踹下了水。
她想都没想就将脑袋缩进了水里。
一直在水里躲着不是办法,体温在流逝,而且这个水塘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根本经不起下水搜。
怎么办怎么办?
没办法了!宴追决定拼一把!
没人注意到,芦苇丛深处,她的身体正贴着泥底下沉。
那件吸饱水的骑士斗篷,沉甸甸的像块铅。
宴追咬碎了牙,死死含住芦苇杆,猛地扎进更深的水里。
水底的淤泥裹着碎石硌得掌心生疼,她胡乱摸起三块拳头大的石头,连同成团的烂泥一起塞进斗篷,用系带死死缠了六道——不够紧!她又咬着芦苇杆,用牙齿辅助拉紧,牙龈被勒得疼,尝到一丝血腥味。
肺里的空气已经耗尽,胸口像被巨石压住,眼前开始黑,耳膜嗡嗡作响。
她知道再不上浮就会窒息,只能借着浮力猛地往上一蹿,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在芦苇叶的缝隙里急促换气。
岸上的疤脸已经在吼:“玛娜!再他妈磨蹭老子射死你!”
就是现在!
宴追攥着“包袱”的系带,手臂因水下阻力和负重抖得像筛糠。她猛地力,将那个裹着石头的斗篷包袱,朝着水塘中央最深的水域狠狠推出去——
“哗啦——咕咚!”
水花溅起半尺高,沉重的包袱带着一串气泡沉底,声响在寂静的夜里像炸雷。
“在那儿!抓住她!”岸上瞬间爆出嘶吼。
所有火把的光全聚向水塘中央,箭矢“嗖嗖”地密集射向水花处,有的扎进水里,有的擦着玛娜的肩膀飞过,吓得女人尖叫着往水里缩。
疤脸的吼声穿透夜色:“围起来!别让她跑了!玛娜,快游过去摸!”
声东击西,成了!
但她的时间不多了。
宴追心脏狂跳得快要撞碎肋骨,朝着与包袱相反的方向游去。
水塘边缘那片芦苇密得能遮住人影,而岸边草丛比人还高。
手臂划水时几乎要脱臼,湿透的衣服裹着身体,每一次动作都带着撕裂般的阻力,只有求生的本能在驱使她往前冲。
离岸边只剩一米!她伸手去抓草根,指尖刚碰到粗糙的草茎,脚下突然一滑,一块湿泥“啪嗒”掉进水里。
这声轻响,却像针一样刺破了嘈杂。
离岸边最近的络腮胡男人猛地转头,火把的光直直扫过来,正好照在她即将探出水面的头顶!
“操!在这儿!”男人嘶吼着举起短弓,箭尖对准了她的方向。
宴追的血液都冻住了。
她想也没想,猛地往水里一缩,箭“嗖”地擦着她的头飞过,扎进岸边的泥里,箭尾还在嗡嗡作响。
她不敢呼吸,憋着最后一口气,像条泥鳅一样贴着泥底往前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