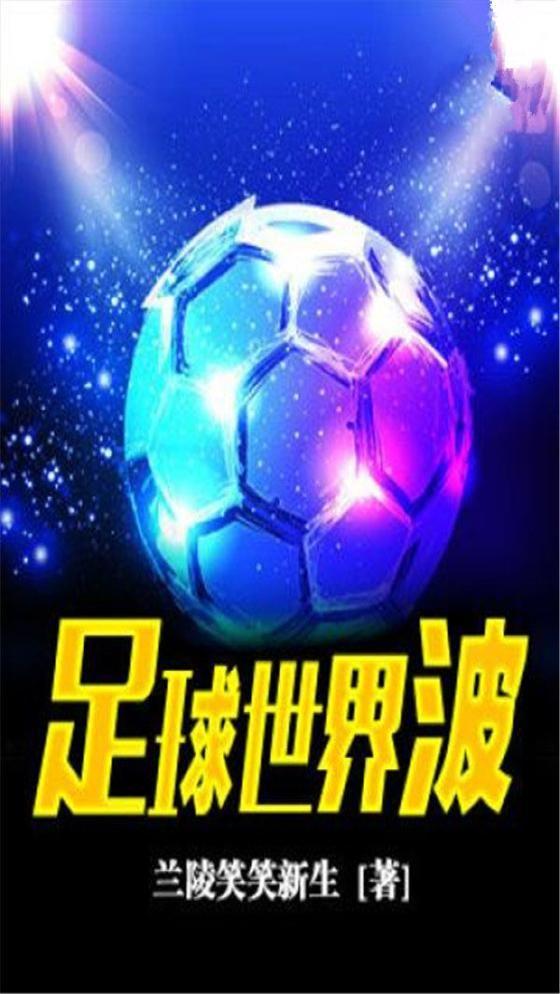366小说>国师他又纯又杀风吹小白菜 > 第105章(第1页)
第105章(第1页)
林蕴霏望进他的眼,半真半假地说:「新法激进,第一步便是清丈土地,皇城中的世家官绅哪个不曾买地占地过?你这是要从他们的口中搜刮走真金白银,谈何容易。」
「你猜陛下为何迟迟不肯推出新法,他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为君者看似凌驾於万民百官之上,凡事皆能随心而治,但事实绝非如此,」林蕴霏不介意将风平浪静之下潜伏的魑魅魍魉指给他看,「他用权衡之术操控着他们,却也为他们所掣肘。」
此乃大昭建国伊始便埋下的祸根,先皇为昭显对有功之臣的亲重,彼时大行封赏丶极力扶持,於是以赵家为首的世家如附在参天之树上的藤蔓,逐渐争夺起天阳之辉,短短数十年内占据了半壁庙堂,甚至隐隐有威胁君主的趋势。
文惠帝上位已有十九年,世家便又兴盛了十九年。
他作为一位打算励精图治的皇帝,怎麽可能没有生出过想要削弱世家的念头?
偏生皇权与世族的力量交杂在一起,动辄损坏国家的根基。
文惠帝为此事头疼不已,一来二去蹉跎数年,仍旧只敢施以浮於表面的敲打。
这些事说是秘辛,但身居庙堂之人皆心知肚明。
以林蕴霏对江瑾淞的了解,倘非搬出这般狠话,他定是不会罢休。
「江大人,明日早朝上你一旦提出新法,不论陛下有无采纳,都将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我,也未必能招架得住来自他们的报复。」
她用清凌凌的双目注视着他,劝道:「总而言之,如今不是实行新法的佳期。」
「谋大事素来不在一时一刻,江大人何妨再等等……」林蕴霏的尾音在面前人暗淡下去的眸光中渐次变低。
江瑾淞缓步走向窗棂,窗牖未有完全关上,依稀能听见楼外的熙攘人声。
他俯瞰着繁华热闹的皇城,心中想的是自己从家乡跋涉至京都赶考那一路的所见。
山野间的哀嚎无法被风吹到皇城,黎民的白骨化为宝马香车下碾过的尘泥。
这些见闻日日夜夜烧灼着江瑾淞的良心,身上的官袍似乎成了滚钉板,扎得他日夜心绪不宁。
此时窗外透过一缕极亮的日光,恰巧照在江瑾淞的眉目间,使得他眸中的阴翳转瞬就被光明驱散。
他偏首看向林蕴霏,轻声道:「殿下可知您与臣在此聊天的工夫里,大昭的某个角落或许就有一位百姓潦倒而死。」
「一日不得革新,百姓便得多受一日之苦,」林蕴霏听着这些振聋发聩的话,几乎不敢去看江瑾淞,「并非臣不能等,而是百姓等不了。」
「臣不惧怕招来那些世族的攻击,他们越是想要索臣的命,说明他们越是惧怕新法,那麽新法之有理便昭然,」青年眸中的烈火一如既往,「假使臣真的为新法而死,心中无怨无悔。」
江瑾淞敛衽对她作揖,只字未提自己的失望:「臣不如殿下高瞻远瞩,知时知势,只恳求殿下勿忘当初向臣许诺的『盛世』二字。」
君与臣思索事情时的出发点不同,产生分歧再正常不过。
江瑾淞完全能够理解林蕴霏的前瞻後顾,但他亦有自己的坚持。
君如轻舟,臣如流水。
林蕴霏面临两难,便该由他这位臣子在前替她溯洄丶成全。
林蕴霏自是听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起身冲他深深地颔首:「我收回适才讲的那些胡话,江大人只管将腹内经纶倾诉於天下,我会尽全力护大人周全。」
「此事与殿下并无干系,」江瑾淞推拒道,「况且大丈夫立身处世,敢做敢当,臣无需旁人来替臣担责。」
林蕴霏却对他说:「江大人是难得的直臣,万马齐喑的朝堂正需要你这般倾心为民之人,便是摒弃一己之私,我也该出手相帮。」
也不知她的哪一个词打动了对方,江瑾淞最终接受道「多谢」。
*
翌日早朝时,户部员外郎江瑾淞在金銮殿上越级上书,提出关於徭役赋税的新法。
新法之要旨极为大胆,引得群臣纷纷交耳相商。
赞同者有之,反驳者有之,身处风口浪尖的江瑾淞与上首端坐的帝王却如出一辙地镇定,仿佛局外人。
待到群臣先後将意见说了个遍,殿内四处飞溅的唾沫落地不见,文惠帝方才幽幽道:「此事争议颇多,又关乎大昭国本,不能马虎相待。容朕回去思虑後,再择时机细说。」
窥见他模糊不清的态度,群臣识相地止住口舌。
然而在退朝後,江瑾淞被文惠帝传旨留下。二人在殿内足足聊了一个时辰,江瑾淞神色沉沉地离开。
除了文惠帝,便只有江瑾淞知晓内情。
果如林蕴霏猜想的那般,文惠帝於私下告诉江瑾淞变法是件如何也急不得的事。
他的想法虽好,但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
将沉疴牵扯出来的代价不可估量,文惠帝无奈地叹息,说,或许眼前的太平皆要被颠覆摧毁。
争权夺利逃不过血光,避不了动乱,而这两者最终迫害的总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