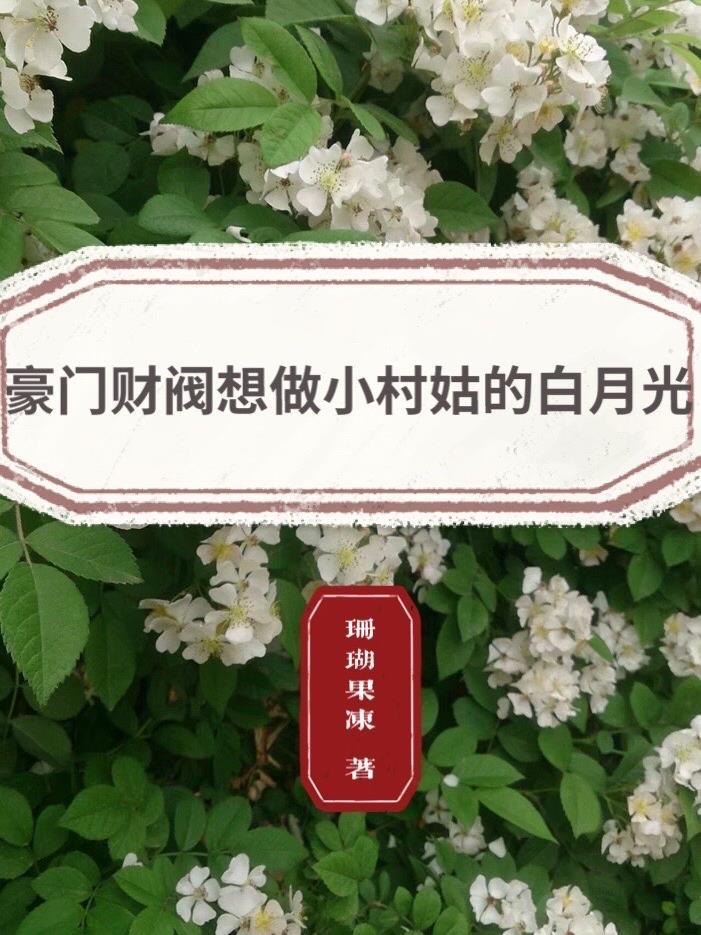366小说>大明:开局炸毁宁远城! > 第60章 炮也能灵活机动(第1页)
第60章 炮也能灵活机动(第1页)
你们虽已走上正途,却未深究其中奥秘。”杜寒惋惜一声,手指轻点炮口,“火炮击发之时,膛内压力极大,气流温度极高,甚至可达三千摄氏度,比我们炼钢炉还要炽烈!”
众人闻言无不惊叹,虽知火炮击发时膛温颇高,却从未想过竟如此惊人。
“肃静!”杜寒伸手示意,人群渐次安静。
“此时膛内受向外膨胀之力巨大,然此力无法全传至外层,离内层越远力越弱,待厚至一定程度,外层几已感觉不到此力。
故一味加厚炮壁无济于事,若仅追求厚重只会徒增重量,毫无意义。”
众人皆面露惊疑之色,杜寒所言之理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即便是王函亦难以接受。
“关键非在壁厚,而在缓解内膛负担,令外层承压更强。
因此炮筒层数越多,抗压能力越强,各层也能更均衡地分摊任务。
此即为何我要将两根炮管嵌套的原因……”
杜寒并未顾及众人表情,继续侃侃而谈:“我们将冷炮管置入热炮管之中,外管冷却时会收缩复原,但内管阻碍其收缩,致使外管紧贴内管。
因内管存在,外管无法收缩至极限,于是始终处于扩张状态。”
杜寒说到这里时,王函似有所悟:“如此说来,火炮击发时内管因发热膨胀,外管随之紧密包裹内管,双层炮管便比单层更坚固,是也不是,百户?”
“不错,正是此理。
看来你悟性极高,若非制炮倒也可惜。”杜寒点头赞许,又同他打趣起来。
王函脸上微红,忙摆手笑道:“岂敢岂敢,百户取笑,造炮岂如考举人有用……”
王函所言极是,确乎正是此意。
杜寒敛去笑意,复又详述火炮之理:“发炮之际,燃气热力欲令内筒向外胀开,然外筒紧束其身,内筒必待恢复原状——即未受外筒压迫之时大小,方能承受张力。
而外筒本已扩张,此刻需再扩张,则必尽力收缩。
内外筒相抗张力,如此较同厚之单层炮管坚韧许多。”
“照此而言,百户所铸巨炮虽看似单薄,实则比红夷炮更为牢固。
若红夷炮亦分双层铸造,便无需那般厚重。”听至此处,刘汉亦有所悟,将此炮与红夷炮相较,论得有条有理。
“汝所言甚是,确实如此。”杜寒亦赞许刘汉,将其朴实憨厚之貌夸得满面红光。
良久,刘汉方觉尴尬,寻了个话题转移方向:
“百户,此炮管虽薄,总令人难以安心,何不在表面加些铁箍?”
“刘匠头,汝此问恰引出另一问题。
发炮时,膛内压力渐减,至炮口处最弱,故强化只应在炮尾。
且看。”杜寒走到炮尾轻拍之,“此即为何在炮尾另套一粗筒,自头至尾加箍实属无益,徒增重量而已。”
此话一出,杜寒便将诸多明军火器彻底推翻,刘汉欲辩无词,因现今新铸佛朗机炮亦去除了铁箍,其坚硬度与旧式铁箍满布者并无多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