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小说>仙门优雅杀猪笔趣阁 > 第188章 新年快乐(第4页)
第188章 新年快乐(第4页)
他不该用怜悯的眼神去垂视自己手中的刀,在以爱之名行以怜惜时,或许他该问问,对于她来说,静置妥善于鞘中,是否真的是她都想要拥有的安宁?
谢允星没有再追着质问男人的动机,也没有过多指责他的擅作主张,那白皙如葱的指尖在桌面上轻划过,她的嗓音永远是那样不会令人生厌的柔和。
“此去一别,怕是数载难见。大人,您不想她麽?”
宴歧认为自己此刻之痛,不亚于被猝不及防被捅了一刀。
这一刀正中心怀,可谓鲜血淋漓。
……
地界,2025年1月28日,除夕夜。
华国,东北地区。
今年看似是个暖冬,哪怕是位于最东北地区的几个省份今年降雪量极少,但就像要映着“瑞雪兆丰年”的吉祥话,赶在除夕夜前,全国会降雪的城市均是紧赶慢赶地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
傍晚时分,大雪未曾停下。
黄昏之下的路灯也被鹅毛大雪覆盖,昏黄的路灯变得模糊不清,大概是大雪压垮了某个部件,在某一刻。那路灯“滋”地一下,竟然是熄灭了。
路边,刚刚走到熄灭路灯下的年轻女人停下了脚下的步伐,长靴的质地在冰天雪地里变得冷硬,她跺了跺脚,低头拢了拢戴在脑袋上的毛茸茸的大衣帽子,抱怨了句:“这天气,飞机倒是还能不能正常起飞啊?”
她只是稍有耽搁,但很快的,像是护着什麽宝贝似的,她又小心翼翼的抱好原本拎在手上的笔记本电脑包,埋了埋头,踩在白雪上的脚下变得更小心,往停机坪方向走去。
在她不远处,是一片开阔地。
开阔地的中央,停着一架飞机,飞机旁又有一辆黑色的加长林肯轿车。
大雪纷飞之下,已经被清扫过一轮的停机坪如今又覆盖了一层新雪,伴随着她“咚”“咚”清脆的脚步声,原本站在飞机下的数人不约而同转过头来。
“南教授!”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作一身西装革履作保镖打扮,转过头便看见一抹冲他们这般小跑奔来的纤细身影——
她身上已经覆盖落满白雪,正常人怕是下意识要用手中拎着的包物遮挡头顶……然而她并未这样做,她甚至反行其道,正小心翼翼将电脑包拢在自己的怀中,用敞开的大衣遮盖着它。
当她逐渐跑进,加长林肯的窗户打开下降一小条缝隙,紧接着一名保镖撑开黑色的伞来到女人的身边。
纷纷落下的大雪被伞面阻隔,她微微一愣,擡起头时,落满白雪的大衣帽子落下,露出其下一张相比起“南教授”这样的尊称,显得过分年轻的一张脸蛋。
小骨架,丸子头,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大概是知道接下来有一趟长途飞行她脸上未施粉墨,却也更显出那双圆润乌黑的杏眼之灵动。
“南教授,您看看您,到了机场可以说一声的嘛,这样大的雪,我们叫人去接您!”
保镖身後传来一声呼声,是一名年纪六十左右的中老年人,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身学术打扮,此时此刻他满脸笑容,冲着年轻女子寒暄。
“顾老师……嗳,您不要跟着这样叫我呀!”黑伞下,整个人都快缩成一只蘑菇的人眨眨眼,“您是想要我折寿噢?”
“哦?那没有的,那没有的——”
两人互相搭话间,已经被簇拥着走上了停在那等候已久的私人飞机。
南扶光,二十八岁,华国最年纪的密码考古学家,研究方向是科技密码考古学。
十八岁那年以省状元的成绩入了华国首屈一指K大,令人跌破眼镜的未选K大好就业丶高发展的王牌专业,而是选择密码与符号考古如此冷门新专业。
本科四年,师兄师姐丶师弟师妹纷纷如何拼命调剂进来就如何拼命转走,唯有她如顽石中扎根青松,从本科至博士,师承本专业大能裴继元老先生。
2019年,3月,裴继元老先生去世。
其一生只收一徒,裴老先生能走後,他的学生成为了华国密码与符号考古学术界内,唯一的扛把子,独苗苗。
同年,7月,世界联合密码与符号考古组织发出呼吁,招请全世界包括不限于华国在内,数个拥有悠长历史文化丶独立神话体系的密码与符号学专家前往一会。
那是南扶光第一次,以华国相关领域话事人如此高大的身份,坐在那麽重要的场合。
当时,身着卫衣和牛仔裤的她一脸懵逼的坐在会场,身边是一大群白发苍苍,肤色丶人种丶性别各不相同的老头老太太,她深深地记得她如何瑟瑟发抖,窘迫的头都不敢擡,仓促地翻开了会议的文件夹。
然後,她看见了让她毕生难忘的讨论话题——
【3与4的整数之间,存在着一棵树。】
……确实,这辈子脑袋上没冒出过那麽多问号。
那时候的南扶光还以为自己疯了才会跑来跟一群疯子开会——
这种议题拿回去科研所,负责报销差旅费的姐姐只需要看一眼,就会拿着扫帚把她赶出来。
报警也是有可能的。
但万万没想到,她之一生也在那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至今日,她坐上了一架私人飞机,这架飞机将去往纽约,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着着名荷兰後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代表作,《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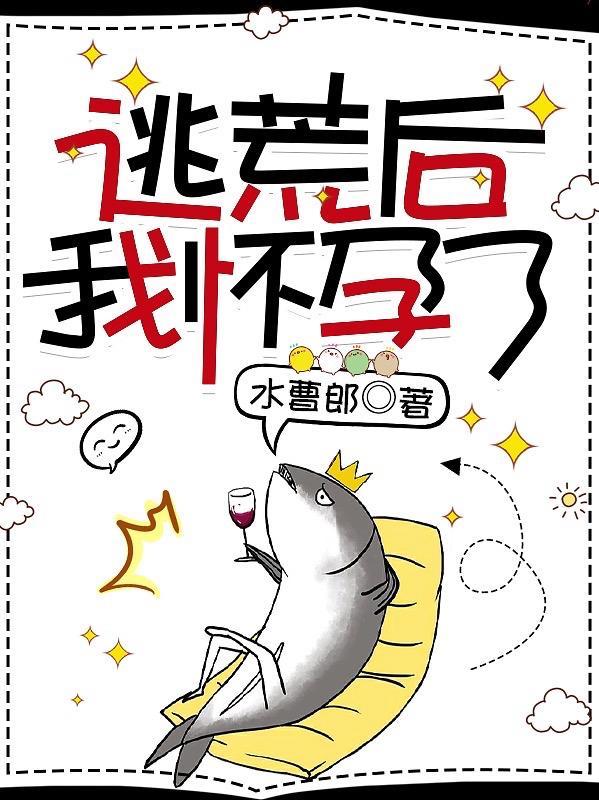
![漂亮反派拿了万人迷剧本[快穿]+番外](/img/5436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