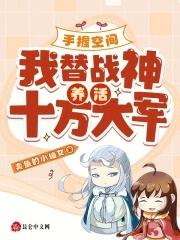366小说>军阀崛起:八美同堂定民国 > 第5章 晚晴通商夏晚晴的算盘与江湖路(第1页)
第5章 晚晴通商夏晚晴的算盘与江湖路(第1页)
(一)江南夏府:烟雨润珠玉,算盘启慧心
光绪二十六年,暮春。
苏州府阊门内的山塘街,烟雨朦胧。青石板路被雨水润得亮,两侧的粉墙黛瓦间,不时探出几枝缀满雨珠的桃花,空气中弥漫着江南独有的湿润甜香。街中段最气派的宅院便是夏府,朱漆大门上悬挂着“江南夏记”的鎏金匾额,两侧楹联“诚信通商通四海,仁心兴业兴万家”,是夏家世代相传的经商信条。
夏家是苏州府赫赫有名的外贸商户,祖上从康熙年间便做起了丝绸、茶叶、瓷器生意。初代先祖本是丝绸作坊的学徒,凭借着对丝绸品质的极致追求和“以诚待人”的经营之道,慢慢积累资本,开设了第一家“夏记丝绸铺”。到了乾隆年间,夏家后人极具商业眼光,打通了南洋贸易渠道,将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运往海外,换回香料、珠宝和西洋货物,生意越做越大,商船往来于苏州、上海、广州乃至南洋,家底殷实,在江南商界颇具威望。
到了夏晚晴的父亲夏鸿儒这一代,夏记的生意更是达到鼎盛。他不仅垄断了苏州府半数的上等丝绸出口,还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分号,与英、法、荷等国的洋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夏鸿儒为人开明,打破了传统商户“传男不传女”的旧俗,只因他一眼看出独女夏晚晴身上的经商天赋——这个女儿,自小就对数字敏感,对货物的优劣有着天生的辨识力。
夏晚晴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出生那日恰逢雨过天晴,晚霞铺满天际,父亲便为她取名“晚晴”,字“锦舒”,盼她如雨后晚霞般绚烂,人生顺遂舒展。她的样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底子,却又透着几分与众不同的灵动与干练:肤白似上好的杭绸,细腻温润,不见半点瑕疵,在江南的烟雨滋润下,更显通透;眉眼如画,眼尾微微上挑,带着天然的慧黠,眼瞳是极深的墨色,看人时专注而锐利,仿佛能洞穿人心底的算盘;鼻梁小巧挺直,鼻尖带着一点自然的粉晕,呼吸间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气息;唇形饱满,唇色是淡淡的樱粉,不笑时透着几分清冷,仿佛拒人千里之外,笑起来时嘴角会漾起两个浅浅的梨涡,瞬间消融了那份疏离,添了几分亲和。
她的头是江南女子少见的浓密黑亮,幼时梳着双丫髻,缀着小巧的珍珠流苏,跑动时流苏摇曳,灵动可人;及笄后便盘成简洁的圆髻,仅用一支羊脂玉簪固定,玉簪的温润与黑的光泽相互映衬,既不失女子的温婉,又不显得娇柔。偶尔她会在鬓边插一朵新鲜的白茉莉,花香清淡,与她身上的气质相得益彰。她的手指纤细修长,指节分明,因常年打算盘、翻查账本、辨识丝绸经纬,指尖带着一层薄薄的茧,却依旧整洁圆润,指甲修剪得整齐利落,偶尔会涂抹一层淡淡的凤仙花汁,透着一股低调的美感。拨弄算盘时,她的手指灵活得像有魔力,噼啪声清脆利落,从无半分差错,仿佛每一颗算珠都能听从她的调遣。
夏晚晴的闺房“晚晴轩”,与寻常女子的绣楼截然不同。窗边没有梳妆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宽大的酸枝木书桌,上面摆满了账本、算盘、罗盘和各地的商情简报;墙上挂着一幅《江南商路图》,密密麻麻标注着贸易路线、各地特产、关税标准,甚至还有不同季节的风向水流;书架上整齐排列着《货殖列传》《商君书》《天工开物》,还有不少外文书籍——那是父亲特意为她请的洋先生教的英语和法语,以备外贸谈判之需。书桌上还放着一个紫檀木算盘,是父亲传给她的,算珠圆润光滑,泛着温润的包浆,是她最珍视的物件。
五岁那年,晚晴跟着父亲去丝绸作坊验货。掌柜的捧着一匹新织的云锦,吹嘘着“质地无双,价值千金”,夏鸿儒还未开口,晚晴便踮着脚尖,伸手摸了摸云锦的经纬,又凑近闻了闻,脆生生地说:“爹,这云锦的经丝不够密,每寸只有七十二根,而真正的上品云锦该有八十一根;纬丝颜色不均,靛蓝里掺了次等染料,用不了半年就会褪色;而且织金的金线纯度不足,里面掺了铜丝,不值这个价。”
掌柜的脸色一变,夏鸿儒也颇为惊讶,仔细查验后果然如女儿所说。自此,他便更加笃定晚晴是经商的奇才,倾尽全力教导。晚晴也不负所望,六岁能熟练背诵《算经十书》,八岁能独立核算中等规模的商号账本,十岁便能跟着父亲参加外贸商会,坐在角落里安静听着大人们谈判,偶尔插一句话,总能切中要害。
十二岁那年,上海分号传来消息,一批运往南洋的丝绸在港口被海关刁难,理由是“货物成色不符”,实则是想索要贿赂。夏鸿儒正在处理茶叶收购的急事,一时抽不开身。晚晴主动请缨:“爹,我去上海处理。”
夏鸿儒犹豫道:“上海鱼龙混杂,海关那些人难缠得很,你一个小姑娘,能行吗?”
晚晴眼神坚定,指尖划过算盘:“爹,经商如打仗,不在年纪大小,在章法。我已经查过,这批丝绸是按南洋商号的要求定制的,成色、规格都有合同为证。海关无非是想要钱,我自有办法应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她带着账本和合同,乘坐漕船赶往上海。到了海关,管事的官员果然百般刁难,暗示要“孝敬”。晚晴不卑不亢,先是拿出合同逐条核对,证明货物无误,又话里有话地说:“大人,夏记在南洋的商号与各国领事都有往来,若是此事闹大,传到领事耳中,说大清海关刁难外商,恐怕对大人的前程不利。”
官员脸色一变,又想作,晚晴接着说:“不过,夏记也懂‘规矩’。这批丝绸盈利有限,若是大人肯通融,后续我们运往欧洲的瓷器,愿意按正规佣金渠道给大人分润——既不违反章程,也不辱没大人的身份。”
一番话既摆清了利害,又给了对方台阶,官员权衡利弊后,果然放行了货物。夏鸿儒得知后,对女儿赞不绝口:“晚晴,你这心思缜密、进退有度的本事,已经远爹了。”
自那以后,夏晚晴便正式参与家族核心生意,从丝绸定价、茶叶收购,到外贸谈判、商路规划,她都能独当一面。她的性格也在经商中逐渐成型:外表温婉恬静,实则聪慧果决、坚韧不拔,既有江南女子的细腻,又有商人的敏锐与魄力,坚守诚信为本,却也懂得审时度势、灵活变通,绝不做亏本买卖,更不与奸佞之徒同流合污。
(二)独当一面:算盘定商路,慧眼识商机
光绪三十四年,夏晚晴十六岁。此时的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为苏州商界有名的“夏小姐”。她依旧喜欢穿素雅的丝绸衣衫,多是月白、湖蓝、浅碧等颜色,裙摆绣着低调的缠枝莲纹,既衬得她肤白胜雪,又不失商人的沉稳。她的眉眼间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干练,看人时眼神清亮,仿佛能看透商机的本质。
这一年,江南遭遇罕见旱灾,桑叶减产,丝绸原料价格暴涨。许多丝绸商号要么囤积居奇,要么高价收购原料,导致市场混乱。夏记的掌柜们也纷纷建议:“小姐,我们也该多囤些桑叶,不然明年的丝绸产量会受影响,利润大跌。”
夏晚晴却摇了摇头,手指在算盘上快拨弄,噼啪声过后,她抬眼道:“不妥。旱灾导致桑叶减产是事实,但高价囤货会让成本飙升至每担三两银子,而且明年若是雨水充足,桑叶丰收,价格必然暴跌至每担五钱,到时候我们会亏得血本无归。”
“那怎么办?”掌柜们忧心忡忡。
“第一,我们不囤桑叶,反而降价出售部分库存丝绸。”夏晚晴指着账本,“现在市场恐慌,大家都在抢丝绸,我们以原价的八成出售,既能回笼资金,又能稳住老客户;第二,派专人去浙江、安徽等地寻找新的桑叶供应地,那些地方旱灾影响较小,我们可以与当地农户签订长期收购合同,以每担一两二钱的合理价格锁定原料,还能帮助农户渡过难关;第三,调整产品结构,减少高档丝绸的生产,增加中档丝绸和棉麻混纺面料的产量,满足普通百姓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
掌柜们将信将疑,但还是按照她的方案执行。果然,半年后雨水降临,桑叶丰收,原料价格暴跌,那些囤积桑叶的商号亏得血本无归,而夏记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因为稳定的原料供应和广阔的市场,利润增长了三成。经此一役,苏州商界再也没人敢轻视这位年轻的夏小姐,都称她“算盘一响,黄金万两;慧眼一开,商机自来”。
夏晚晴的经商才能,不仅体现在应对危机上,更在于她对商机的敏锐洞察。宣统二年,她在上海参加外贸展会,看到洋商带来的“洋布”虽然质地不如丝绸,但价格低廉、耐磨耐洗,深受普通百姓喜爱。当时许多江南商户都不屑于做洋布生意,认为“有损丝绸世家的体面”,夏晚晴却从中看到了潜力。
她立刻派人调查洋布的生产工艺和市场需求,现洋布的核心优势是价格(每匹仅需五百文)和实用性,而短板是花色单一、手感粗糙。她果断决定:“我们不做纯洋布,而是做‘丝洋混纺’。用江南的优质生丝混合洋布的棉纱,改进纺织工艺,既保留丝绸的柔软光泽,又兼具洋布的耐磨特性,花色按江南审美设计,定价每匹一千二百文,介于丝绸(每匹三两)和洋布之间。”
这个决策遭到了家族长辈的反对:“夏记世代做丝绸,怎么能降格做这种‘杂布’?”
夏晚晴耐心解释:“经商之道,在于顺势而为。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丝洋混纺既能满足普通百姓对品质的需求,又能让我们开拓新的市场,何乐而不为?而且,这不是降格,是创新。”
她亲自盯着作坊改进工艺,反复调试生丝和棉纱的比例,设计出牡丹、莲荷、缠枝等传统花色。产品一经推出,立刻供不应求,不仅在国内畅销,还通过外贸渠道销往南洋,成为夏记新的盈利增长点。洋商们也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女商人刮目相看,纷纷上门寻求合作。
此时的夏晚晴,已经成为夏记实际上的掌舵人。她每天清晨便到商号处理事务,中午在商号简单用餐,下午要么去作坊查验产品,要么接待客商,晚上则在晚晴轩里分析账本、研判商情,常常到深夜。她的手指因为常年打算盘,指尖的薄茧愈明显,但她依旧保持着江南女子的精致,指甲修剪得整齐圆润,涂抹着淡淡的凤仙花汁,透着一股低调的美感。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她的性格也愈鲜明:沉稳冷静,遇事不慌,无论面对多大的商机或危机,都能凭借算盘和智慧算出最优解;诚信为本,与她合作的客商都知道,夏记的账本从无虚数,承诺的交货期从不延误,因此口碑极好;坚韧果决,一旦做出决策,便会雷厉风行地执行,不拖泥带水;同时,她又不失温柔与同理心,对待商号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合作的农户,都宽厚体恤,逢年过节会送上福利,遇到困难会伸手相助,因此深得人心。
(三)乱世惊雷:商路断,父病倒,临危受命
民国元年,辛亥革命爆,军阀混战的阴霾迅笼罩全国。对于依赖南北物流和外贸渠道的夏记而言,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先是北方战事频,铁路、公路被军阀控制,夏记运往北平、天津的丝绸、茶叶被拦劫数次,商队人员也有伤亡;接着,沿海港口被各路军阀割据,关税暴涨,外贸渠道受阻,运往南洋、欧洲的货物积压在仓库,资金无法回笼;更严重的是,各地贪官污吏趁火打劫,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都要面对层层关卡、高额勒索,许多商队因为不愿行贿,货物被扣押,血本无归。
短短半年时间,夏记的生意一落千丈,上海、广州的分号接连亏损倒闭,苏州总号的仓库里积压了价值十万银元的货物,资金链濒临断裂。夏鸿儒日夜操劳,四处奔走寻求解决方案,却屡屡碰壁,加上忧思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卧床不起。